去年圣诞节前,我跟斯坦福商学院二十几位同学一起,在孟买和班加罗尔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参访,重点是印度的“数字革命”。时隔一年,终于提笔,与大家分享我印度之行的收获。这是印度考察系列的第二篇。】

在我印度之行的几个月前,我的一位印度同学到中国参访了两周。她说,去中国前,她以为印度比中国落后四五年,去之后,她意识到差距得有十年。基于我印度之行的认知,我觉得她还是太乐观了。
没去印度之前,我想象中,印度和中国都是泱泱大国,都是高速发展的经济体,都有充沛的廉价劳动力,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所以印度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就是几年的时差问题。然而,尽管我在印度短短十天的认知必然不全面和有偏颇,已然足以颠覆我之前的看法。
印度与中国除了都人多,其他方面差异太大了。最大的差距在于基础设施,包括能源水电、交通、卫生系统,以及对未来发展极为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的落后在印度当前环境下很难快速改善,将严重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潜力。跟中国经济的差距不是十年或二十年,而是会越拉越大。就看印度政府是否能把握住数字经济这个变道赶上的机遇。
以交通为例。印度对铁路交通依赖程度很高。亚洲第一大贫民窟达拉维旁边就是一个铁路运输枢纽,对达拉维发展成10亿美元的经济体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印度的铁路系统还是一百年前英国殖民时代的遗产。铁轨公里数不短(6.6万公里,世界第四长),但是更新缓慢,疏于维护(铁轨常被垃圾淹没,被动物尿液腐蚀,年久失修),技术严重滞后,造成事故多发,火车速度慢,常晚点。全国有四种铁轨制式,所以需要频繁换车,进一步拉低了效率。

(铁轨变成垃圾场)

(孟买贫民窟千人洗衣厂旁的铁轨)
2500万人口的孟买只有一条地铁线路(应该算城铁吧,很多轨道在地上而不是地下),2014年才通车,另有两条地铁线在建。
我在孟买看到的地铁车厢都没有门(不知道是根本没有门还是门永远敞开着),很多人挂在门口,车进站还没停稳,乘客就跳上跳下。我问印度同学,车厢看起来并不拥挤,他们为什么挂在门边,而且行驶的列车为什么不关门?同学说,“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凉快、拉风吧”。
商业中心孟买只有一条地铁线路,那市内交通的压力主要在马路上。孟买同向双车道的马路已经算是主干道,汽车、摩托车、人力拖车、行人,还有动物,神奇地交织在一起,不堵车才是怪事。

(孟买街头)

(霸道神牛)
没有找统计数据证实,我在印度那些天的体验是,班加罗尔的交通拥堵比孟买还要严重。一个小时的参访活动,往返路上需要四个小时。这样的交通状况,不仅浪费时间降低效率,还因为交通时间的不可预测性,增加了商业活动成本。
我们到访时,印度头部电商Flipkart正在为提高全国物流配送的效率大伤脑筋。糟糕的交通基础设施带来的效率损耗,不是互联网公司的科技可以弥补的。
数字基础设施同样薄弱。
我们拜访的印度移动打车平台Ola的负责人说,创业初期,核实一位Ola司机的身份需要花一个月时间。司机驾照由各地方政府颁发,很多是手填的,根本没有官方的线上数据库可查,需要通过书信电话方式到各个地方政府查询,效率太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只能妥协,后来就只查司机的指纹,确认这个身份对应着一个真人即可,也没有途径查询司机的犯罪记录。
基础设施的落后,跟印度的政体、种族文化、社会结构等密切相关。
政治体制
印度号称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不过世间没有完美之事。我一路无数次听到印度人把各种问题都归咎于政府官员的官僚和腐败(言论自由大大的有,但是感觉他们也没有解决腐败顽疾的药方)。
孟买满大街触目惊心的垃圾,我问印度同学,印度劳动力这么便宜,政府为什么不雇佣清洁人员,保持市容整洁呢?回答是政府太官僚太腐败了,他们不作为。
我在贫民窟达拉维看到张贴着当地政客的竞选海报时,问当地人的看法,听到的回答是,这不过是作秀,这些政客靠花钱贿赂百姓买选票,上了台要拼命敛财连本带利捞回来,而百姓也有他们的招儿,鸡呀粮食呀小恩小惠照收不误,投票时到底投了谁的票只有自己知道;又说投谁其实都差不多,反正都是官僚和腐败。
另一方面,印度是联邦制政体,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和资源做大型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通过废钞和税制改革等一系列动作,对打击腐败、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印度各邦分治力量强大,加上民族语言宗教等的巨大地区差异,中央政府很难做全国的顶层战略设计和统一高效实施。
中国式的高铁工程,在印度政体下不可能发生。莫迪2014年提出了高铁计划,2017年印度第一条高速铁路开工。然而没过多久就搁浅,因为印度土地私有,加上地方政治复杂,农民暴力抗议,征地难度非常大。
在印度邦一级,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治斗争提高了商业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2008年,塔塔集团有意在西孟加拉邦设厂生产Nano汽车,当时该邦的执政党认为这是增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的长期利好的事情,承诺给予塔塔很优惠的贷款、税收等政策条件,并积极帮忙征地。但是,没能与部分农民达成征地协议。由于该邦次年即将大选,反对党印度国大党抓住这个机会拼命搞事情,煽动农民暴力冲突,放火烧毁了塔塔已经建好的厂房等设施,最终迫使塔塔放弃已经投入的数十亿美金投资,离开西孟加拉邦,重新选址。
土地私有、公私合营、政治斗争、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使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步履维艰。
语言文化
印度有一百多个民族,数百种语言,上千种方言。官方语言就有22种,其中印地语和英语是联邦级官方语言,其他是邦级官方语言。全国约40%的人会讲印地语,20%的人会讲英语。我们一行中有四位印度同学,他们各自的母语都不同,靠英语交流。
印度不仅是人种博物馆、语言博物馆,还是宗教博物馆。不同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的人,有着多元的消费需求。
Ola说,他们的APP有十几种语言版本,印度的科技创业公司APP大多在首发时就提供多种语言版本。亚洲最大的卫星电视台STAR一再向我们强调印度多语言多文化的独特性,STAR针对不同语言的受众要制作完全不同的内容,而不只是增加字幕翻译和配音。
从这个角度看,印度虽然人口众多,但并不像中国一样是个相对统一的大市场。
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对印度的影响不仅是需求多元化和市场碎片化,更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统一凝聚力。美国也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美国是个强大的文化熔炉,有美国宪法、美国精神、强势的英语将移民都变成美国人。而印度社会则松散很多,也很难讲清楚印度精神、文化内核到底是什么。缺乏大一统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全国性的战略规划在地方频频受阻,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跨邦开展。
种姓制度
三千多年前,雅利安人开始南下进入到印度河流域,打败了土著的达罗毗荼人,逐步称霸印度北方。但是雅利安人人数少,为了维持统治,把人划分成几个阶层管理,逐渐形成了种姓制度,并通过宗教让低种姓的人服服帖帖地认命受压迫,寄希望于下辈子投个好胎。
种姓由高到低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婆罗门是最高种姓,自诩是神的代言人,担任祭司。刹帝利是武士和官吏阶层,管理国家军事和行政事务。吠舍是平民种姓,主体是小工商业者和农民。首陀罗是低种姓,做重体力劳动和奴仆,几乎都是非雅利安人。
此外,还有一个“不配”进入种姓体系的贱民阶层——达利特,被认为是低贱肮脏不可接触的,从事掏粪、背尸、屠宰等污秽之事。我在印度街头看到提着鞋子光着脚走路的人,印度同学告诉我,他们一定是达利特。
种姓制度最主要的限制在于婚配和职业两方面,不同种姓的人世世代代被割裂封闭在不同的圈层中,让阶层流动成为不可能。
在当今的印度,表面上看,种姓的影响力日益式微,从肤色、姓氏、职业,都不能准确判断出所属种姓,询问种姓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
印度宪法禁止基于种姓的歧视。为保障低种姓的政治和受教育权力,议会、政府机构、公立学校都给首陀罗和达利特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
但是,现实生活中,种姓制度根植于印度宗教文化几千年,其无孔不入的影响力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消除的。
种姓观念在当今印度社会最主要的体现在婚姻方面。虽然越来越多开明家庭接受跨种姓的婚姻,财力和种姓仍是双方家族最看重的因素。特别是高种姓的女子不可以嫁给低种姓的男子,此种婚姻被家族反对引发的人间悲剧仍不时在印度上演,播下仇恨的种子。
教育是如今低种姓跨越阶层改变命运相对最可行的途径,越来越多的低种姓家庭认识到送孩子上学的重要性。但是,低种姓的人,特别是达利特,有可能自惭形秽或者被歧视排挤(尤其在农村和偏远地区),不敢跟高种姓的孩子一起去上学。他们世代做着最底层的工作,目不识丁,在现代社会仍然无力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政治上,低种姓出身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些政客获取底层选票的政治工具。印度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一人一票的投票权,达利特约占印度人口的16%,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然而,种姓出身与政治选举的结合,更加剧了印度社会的割裂。
另外,种姓制度的“天命”思想,让特权阶层坐享其成,不思进取;让被压迫阶层,逆来顺受,卑微认命。这必然会束缚印度社会的奋斗精神和创造能力。
结论
近几年,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增长放缓,资本和创业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印度,希冀通过复制硅谷或中国模式,假以三五年的耐心,就可以再造印度版的腾讯和阿里巴巴。
我的印度之行结论是,长期可期待,短期不乐观。
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必然带来商业活动效率损失;联邦制政体下中央政府势弱,缺乏顶层设计和政令有效施行的能力;贫富差距以及种族语言文化宗教的多样性,造成社会割裂和市场严重碎片化;且宗教和种姓制度依然束缚着印度社会阶层流动的活力和创造力。
印度的金融中心孟买,市内散落着大大小小近两千个贫民窟,钢筋水泥玻璃幕墙的高楼大厦旁边,就是木板、石棉瓦、防雨布搭起来的棚户区。我的印度同学说,孟买是印度发展最早的商业中心之一,很多年前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贫民到这里讨生活。孟买气候温暖,随便找块无主的地方支个帐篷就能安家,亲戚老乡拖家带口生儿育女,人越聚越多,慢慢地发展成连片的贫民窟。
当政府有了城市规划意识,因为种种原因(土地所有权、选票、就业、住房再安置等问题)已经没办法把他们搬迁走,就形成了孟买城中豪宅区与贫民窟毗邻交错的奇观。

(孟买千人洗衣厂,据说孟买三星级以下酒店的床单都送到这里人工洗涤)
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贫民窟达拉维(Dharavi)就坐落在孟买市中心。不到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着一百万人。
我们在达拉维的导游就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一群大学生,他们合伙创立了一个导游社,专门带游客游览他们引以为豪的家——达拉维。他们认为,与其让观光客走马观花地拍些猎奇的照片满足窥探欲,不如由他们达拉维人亲自带游客更深入地了解达拉维的奇迹和精神。
达拉维分为两个区域,商业区和住宅区。
一平方多公里的商业区聚集着一万多家小微企业,年产值高达10亿美元。主要产业有皮革业、制衣业、垃圾回收加工业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个高效运转的产业体系,链条成熟,分工细致,无缝衔接。然而据我观察,产业还非常初级原始。这里的小微企业,实际上就是一间一间十几平米的手工小作坊,基本靠人力和简单的工具进行生产。

(达拉维商业区街景)
从事制衣业的很多,每隔几间房,就可以看到织布、漂染或者制作成衣的小作坊。染布的作坊,在角落里砌一个池子,旁边摆着花花绿绿的颜料桶,颜色艳丽的水里泡着布,浸泡完毕,就悬挂在屋子另一侧拉起的绳子上晾干。隔壁可能就是挤着四五台缝纫机的昏暗的制衣车间,几个印度小伙子埋头缝制廉价的沙丽,顾不上抬头看一眼我们这些外来访客。

(染坊一角)
皮革业的车间规模相对大一点。我在达拉维看到一块皮革从离开动物身体到变成一只皮包的全过程。业主很有品牌意识地为成品注册了达拉维商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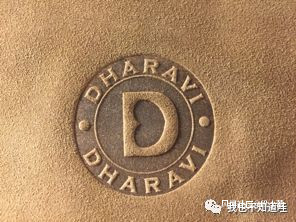
然而我在这里看到的皮革加工仍然很初级,机械化程度低,产品标准化程度低,远达不到工业化生产水平。

(皮革处理车间)
达拉维到处可见废品回收再加工的作坊,我甚至感觉是垃圾产业养活了达拉维人。


垃圾运到这里,先人工分拣。一堆塑料垃圾里,有酸奶瓶、矿泉水瓶、饭盒、洗发水瓶、输液用的胶管、拖鞋、旧玩具、塑料桶,无所不有。

几个人蹲在一堆垃圾里熟练地把塑料按相似颜色分拣开,然后放进一个大盆里简单冲洗,再放进手摇的小机器里粉碎成颗粒状,装进大编织袋。这个小作坊的处理流程就结束了。塑料颗粒卖到下一个环节,下游客户可能就是几十米开外的另一间小作坊。
拐个弯走进下一条巷子,是几间处理金属垃圾的作坊,屋外摆着很多铁桶锡桶,屋里搭有简易的熔炉。


导游说,达拉维的垃圾来源复杂,可能混有未经处理的医用垃圾或化学垃圾。政府规定工人处理垃圾时必须戴口罩和手套,但是很多工人觉得不方便不舒服或不习惯,巡检人员一走就摘了口罩手套,也将自己的健康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中。

达拉维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我看到工人坐在泥地上徒手分拣着垃圾,脚边有老鼠旁若无人地窜来窜去,而隔壁邻居可能是牛或羊。

(来自达拉维羊羊羊的问候)
工人们就住在这些小作坊的二楼。达拉维商业区的房子基本分上下两层,下层是生产作坊,上层住着工人。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能赚3至10美元。
达拉维的工人要么在贫民窟出生长大,要么是来自农村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在农村无以为生,只能背井离乡讨生活,大城市的贫民窟就是他们新的安身立命之地。在这里至少可以凭借劳动生存下去,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长时间的劳作都是可以忍受的。在我们看来极为艰苦的贫民窟,条件甚至可能好于其原来的生存环境。有的人在达拉维扎下根安了家,有的则从一个贫民窟到另一个贫民窟,打着零工,漂泊不定。
达拉维的住宅区相对干净很多,更有温馨的家庭气息。
上下两层石棉瓦屋顶的房子隔成一个一个鸽子窝,密密地排在一米宽的小巷两侧,也有些三四层高剥落了墙皮的旧楼房,空间逼仄,但是整体看来又井然有序。半开的门里,祖母一边缝补一边照看着爬来爬去的孙女。门外,狗狗懒洋洋地躺在地上。孩子们穿着整齐的校服,无忧无虑地在巷子里追逐打闹。街角有较开阔的公共空间,立着板凳,挂着秋千。透过敞开的窗户,能看到达拉维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课堂。这是一个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世界。

(达拉维住宅区街景)
达拉维的住宅区有印度教的神庙,也有穆斯林的清真寺。穆斯林相对集中的聚居点,街上悬挂着穆斯林旗帜。达拉维极具包容性,不管什么背景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容身之处。
导游骄傲地告诉我们,达拉维的治安很好!邻里和睦,互帮互助,鲜有偷盗和抢劫,犯罪率很低。(关于达拉维的犯罪率,我并没有更多信息来源证实。)达拉维人认为他们创造了达拉维的一切,是达拉维的主人,也有责任维护达拉维的秩序。
达拉维人对这里有强烈的归属感。有的家庭四代人都住在这里,在达拉维出生、上学、工作、老去。有些年轻人离开达拉维去读大学,毕业之后又带着新组建的家庭回到这里。有些人在这里经商多年,早就脱离了贫困,却不愿离开达拉维搬去更舒适高档的社区。
达拉维的房价相当不便宜。
当我从导游那里听到达拉维的房价一平米约合人民币两万五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开玩笑吗?2015年北京通州的新楼盘均价不过两万出头,国贸CBD背着LV通勤的小白领们在通州买房还得贷款,孟买贫民窟的人如何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而且通州的板儿楼南北通透配套完善,跟贫民窟的蜗居怎能一个价?我特意又向印度同学求证,竟得到了差不多的数字。
得知几百米开外那一片干净敞亮的商品房平米单价比达拉维还便宜时,我更惊讶不已,那达拉维人为何不住那里?达拉维没有全天供水,时常断电,上千人共用一个厕所,一大家子人挤在十几平米的小空间里,有的房间甚至没有窗户。为何房价如此之高,而且有活跃成熟的不动产交易市场?我百思不得其解。

导游解释说,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这里的房子面积小,单价高但是总价低。贫民可以花25万人民币给一家人在达拉维买个10平米的小窝;而旁边的商品住宅楼,尽管每平米单价略低一点,但是一套两居室总价要200万人民币,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即。
第二,达拉维虽然看起来破破烂烂,但是个年产值10亿美元的经济体。这里有很多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地理位置又处在孟买市中心的黄金地段,毗邻铁路,交通便利,其商业价值决定了房价自然不会低。
第三,达拉维的人口密集度很高,住房需求旺盛。不仅有全国各地源源不断新输送来的农民工,土生土长的达拉维人即使有能力离开贫民窟也不愿搬走,甚至在这里买下多套房子或商铺做包租公包租婆。
达拉维人创造了奇迹。依靠如此贫瘠的资源,养活了上百万人口,而且还向政府缴纳了可观的税款(10亿美元经济体正是通过向政府的纳税额推算出来,实际产值可能更大)。
达拉维看似混乱,实则是个运作严密有序的社区。一万多个商家,百万人口,背景复杂却能和谐共存,自组织自治理能力令人惊叹。
按照导游所说,达拉维人热爱这里,以身为达拉维人而骄傲。他们辛勤劳动,努力生活,邻里和睦,充满了人文精神。
贫民窟达拉维看似已经形成了自洽和谐的生态,然而却隐藏着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的问题。
1.印度工业化水平低
达拉维的小作坊是印度轻工业和制造业的代表。上万个小作坊,每个却只有几个雇工手工劳作,没有形成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水平初级,生产效率低下;但是达拉维年产值总量能够达到10亿美元,产品行销全国。这说明在印度,这样的生产力水平是具有竞争力的。窥一斑而知全豹,反映出印度的轻工业和制造业整体水平还很落后。
我查了一下相关数据。2018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仅占印度GDP的14.9%,而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2%。从全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都是在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始兴盛,否则极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印度的第一第二产业羸弱,粮食和工业品都严重依赖进口。50%的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并没有能够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体现出人口红利。这种经济结构与印度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且埋下了危机。
莫迪上台后,看准了印度经济的软肋,提出“高铁计划”和“印度制造”战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工业化水平,政策方向是对的,然而实施起来却步履蹒跚。在印度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莫迪纵有鸿鹄之志,也只能一声叹息。(关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困境,参见《印度落后中国多少年?》)
简而言之,印度的工业化之路有以下障碍:
1)基础设施差,特别是交通运输系统和能源电网支撑不了工业化大生产;2)土地私有制和地方选举政治加剧了征地困难,推高了实业投资的成本和不确定性;3)官员腐败低效和政策缺乏连续性阻碍商业资本大规模投资;4)大部分人口受教育水平低,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不足;5)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新兴世界工厂的竞争。
回想亚洲四小龙,无一不是在威权政府治下靠发展“低人权”的制造业起飞,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付出了血汗工厂、环境污染的代价。印度自1947年独立起就实现了民主政体,且联邦制下没有中央集权,印度制造业大国的梦想考验着莫迪的政治智慧。
2.印度大量失地农民涌进贫民窟
贫民窟源自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占地聚居。印度土地私有,然而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20%的家庭占有80%的耕地。根据印度学者Aparajita Bakshi的研究数据,2005年印度农村每千户中428户没有耕地,“贱民”达利特则有57.4%的家庭没有耕地,且达利特的失地趋势在加剧。
印度宪法保障公民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大量在农村无地少地失去生计的贫民涌入城市寻找生存机会。在城市中没有明确产权的土地上,穷人可以搭篷而居,居住达到一定年限,就成为所占土地的主人。
这些贫民,在农村失去耕地,退无可退;印度制造业落后,又没有如同中国当年的深圳、东莞的工厂可以吸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些失地农民涌进大城市,由于缺乏技能没有文化,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劳动。达拉维的垃圾回收业是典型的贫民窟产业。
当贫民窟形成一定规模后,居民依照法律获得了所占土地的所有权,登记成为选民拥有了投票选举权,事实上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政府或房地产开发商如果想要拆迁贫民窟,除了必须要取得居民的同意外,拆迁补偿、住房保障,以及就业安置,都是巨大的挑战。
农村失地农民大量进城,而城市消化不了这些低端劳动力。再加上自由迁徙和居住、土地私有制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体,印度贫民窟的存在成为无解的问题。
3.印度社会阶层固化隔离
种姓制度在印度有三千年的历史,虽然已被法律废止,世世代代的阶层隔离却固化在社会观念中,集中体现在教育、就业和婚配上。
前文讲到“贱民”达利特是印度农村失地比例最高的社会阶层,他们是贫民窟居民的重要来源。
达拉维人世代居住在贫民窟,貌似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和超然于世的社区。然而,当受过教育、有了一定经济能力的达拉维人依然认为他们归属这里,固化在人们头脑中的“阶层归属感”如何打破?印度社会阶层的流动何时才能实现?


